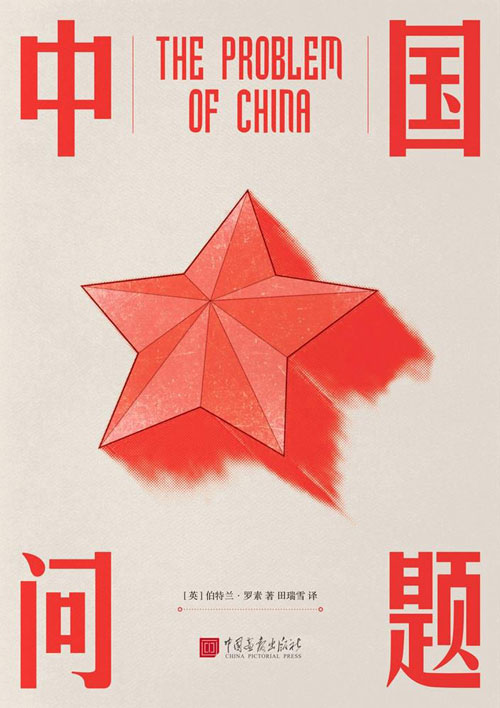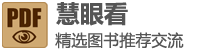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罗素博闻强识,其外祖父曾任英国首相,自然而然,罗素对中国的见识看法要比西方人甚至中国普通读者更为细腻深刻。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北京讲学一年,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学术上发生精彩的碰撞,随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罗素于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他代表作品有 《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社会重建原则》等。
译者:田瑞雪,1984 年生,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管理学学士。一级翻译(CATTI 英语一级笔译)。职业翻译。每日笔耕不辍,时时警勉,定心神,戒虚荣,痴心不改。本业之余,闭户读书,洗心涤虑,低头独长欢。
目录
序一 罗素的“中国问题”,中国之“罗素问题”(童世骏)
序二 中国人的确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储殷)
第一章 种种疑问
第二章 19世纪前的中国
第三章 中国和西方列强
第四章 现代中国
第五章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第六章 现代日本
第七章 1914年前的中国和日本
第八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和日本
第九章 华盛顿会议
第十章 远东当前各种势力及趋向
第十一章 中西文明对比
第十二章 中国人的品格
第十三章 中国的高等教育
第十四章 中国的工业
第十五章 中国前景展望
附录
译后记
前言
序一 罗素的“中国问题”,中国之“罗素问题”
童世骏
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很多,但只有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出自一位哲学大家之手。近代以后访问过中国的西方哲人很多,但只有这位英国哲学家,在中国讲学将近十个月以后,出版了这本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
对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中国问题”一词可能有点陌生。从孙中山在1904年8月31日撰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到邓小平在1990年12月24日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问题”这个词逐渐少用,以致几乎匿迹。
但恰恰在这样的时刻,伯特兰·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却特别值得一读。
首先是因为,在这本书中,作者早在将近百年以前,就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做出了确切预言:“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中国哲学家梁漱溟先生曾在1972年撰文夸奖“英国哲人罗素50年前预见到我国的光明前途”;但真正体现罗素中国观之预见性的,还是在进入世界的新世纪以后,尤其在进入中国的新时代以后。
但罗素在这本书中不仅讨论了“中国问题”,而且提出了他自己有关中国的一个问题:走出积贫积弱之后的中国,会是一个怎样的国家?罗素说他很担心,在为独立自主而变得强盛的过程中,中国人会不会最后也走上帝国主义之路呢。在罗素看来,为求自立自强,中国固然要向欺侮她的西方列强(及其东方模仿者即日本)学习科学和技术、工业和军事,但中国如果在由此战胜列强以后却也像后者那样恃强凌弱,如果在掌握了实现价值的有效工具以后却把公正价值弃之不顾,那么她可以说是名胜而实败、外赢而内输了。罗素在《中国问题》中一再表达的这个忧虑,或许可称为有关中国的“罗素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经在长沙听过罗素演讲,并且在其有关中国未来之思考中认真研究过罗素建议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用罗素并不赞同的手段创造了罗素的“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的根本条件之后,对中国之“罗素问题”可以说是有过明确回答的。1949年9月21日,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同时,毛泽东就强调这意味着“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两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同样意思,尤其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时候,他撰文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并强调我们要永远保持谦虚,“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沙文主义”。
60年后,在2016年11月11日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同志以与时俱进的方式重申了一脉相承的承诺:“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各国都发展得好,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我们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
按照“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从十八大以来,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尤其从当前的中美关系来看,中国要消除罗素在一百年前表达的那种担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其中包括在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发展的国际条件和世界意义的基础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进行更有成效的对话和沟通,并且把这种对话和沟通,也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时代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的重要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由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革命这三个方面构成的复合体;在中国发展的当今阶段,其实从一开始就渗透在这三方面之中的第四个方面即“贡献人类”(毛泽东在建党前夕就强调“中国的改造”与“世界的改造”是密不可分的),从后台走向了前台,从而要求我们通过四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诠释和相互支撑,来理解和推进我们的伟大事业。
先于罗素一年到抵达中国、与罗素同日离开中国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撰文对罗素的《中国问题》做高度评价,称赞该书为“最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最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但杜威也指出,这本书的读者如果不考虑其作者是在对西方文明极度失望的情况下“去中国寻找新的希望”的,“将会错失本书主要的深远意义”。在杜威看来,在这本书中,“中国往往变成了一个闪亮的天使,以便表现出西方文明的阴暗。中国人的美德被视作一根鞭子,用以鞭打自鸣得意的西方人的后背。”关于罗素此书的读者对象和写作本意,杜威说的基本不错;但说罗素几乎没有触及“中国内部的问题,即它的文化和制度的转变”,杜威却有不够公平之嫌。其实,对于此书出版后将近百年的中国读者来说,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而且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这些都是不难找到的;从这种展望和议论中得到有利于我们解决自己问题的启发,也是可以期待的。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在百年之后仍然值得在中国重译再版,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在今天语境下阅读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除了上述实质性的理由以外,也有方法论上的理由。罗素在此书开篇就强调中国问题的重要性;针对这种重要性他不仅投入了相匹配的研究精力,而且动用了多视角的研究资源。罗素讨论中国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问题,这固然限制了他的中国研究的视角和深度,但对中国读者来说,这种研究进路却未尝不可以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包括在1965年的重印本序言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期待;就我们在当代世界参与国际对话——尤其是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对话——的努力而言,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欣赏罗素的这种态度,而是同时要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像罗素那样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果这样的对话者在客观上越来越少了的话,我们则要思考,如何通过我们更多更好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
2019年5月26日于上海松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