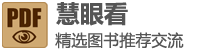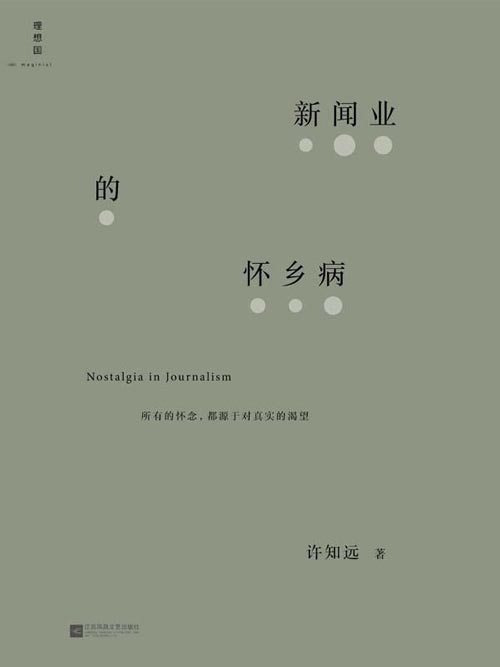
编辑推荐
-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新闻业何为?
面对通稿和“10万 ”,还存不存在严肃的新闻业?在历史上,一代代媒体人怀抱着何种梦想投身其中,用自己的雄心和才华重新定义新闻业?
- 媒体人如何捕捉新时代的风尚,《纽约客》可以告诉你答案
纽约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使得家乡暗淡无光,享乐主义更具诱惑力。举止粗鄙的罗斯*终创造出《纽约客》,是因为他成功地捕捉到新一代纽约人对于幽默感的理解。
★ 避免取悦他人,不管是权力、市场还是公众
2001年度风云人物评选中,《时代》编辑踌躇再三,*终选择了纽约市前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而不是本·拉登。很显然,在尊重客观与讨好公众之间,《时代》选择了后者。
- 判断力比勇敢更重要
中国新闻界有两种人:有的人将自己想象成斗士,认为只要尽可能地披露真相,就越可能接近真理;也有人将自己的平庸推卸在制度层面上,抱怨所受的阻拦,而只要面前这座大山消失,前途必然光明。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媒体评论集。许知远从新闻从业者的视角,聚焦《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财富》《经济学人》《连线》等传媒巨擎,对它们的经营理念、发展历史、未来走向进行了有益的梳理,展现了这些传媒帝国的媒体精神。作者回看这个行业的往昔时,在书中漫生出来的尊敬、怀念,以及乡愁般的忧伤,对于今天的新闻从业者和媒体研究人员都不无借鉴作用。
作者简介
许知远,作家,单向空间联合创办人,《东方历史评论》主编,访谈节目《十三邀》主持人。代表著作有《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新闻业的怀乡病》《醒来》《一个游荡者的世界》等。
前言
如何捕捉时代风尚
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变化惊人。在工业界,福特汽车公司正在驱动股票市场强劲增长,新生的广播与电影业让年轻人惊叹不已。文学界与艺术界正在遭遇洗刷,爵士乐令人兴奋,夜间俱乐部不断增加,百老汇是谈话的焦点。钢铁的摩天大楼暗示着新一代对于未来的无比信心,就像查尔斯·巴斯克威利所说的:“对于年轻人,那是个无比亲密的世界,他们努力去创造、拥有快乐的生活。”
一个新时代的纽约人需要怎样的一本杂志?编辑天才哈罗德·罗斯敏感地意识到,当时的报纸与杂志似乎还未把握住新时代的精神,要么仍被普利策、赫斯特的煽情新闻影响,要么像《大街》中的人物一样仍沉浸于狭隘的乡镇趣味中。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在为别人编辑《判断》杂志时,他的老板经常会要求罗斯去报道类似教区扫雪的事件。罗斯知道,纽约的新青年们没有谁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他们想知道百老汇的最新剧目,更想学会一些机智的俏皮话以便在夜间聚会时炫耀一番。尽管有《名利场》《美国水星》这样的竞争者,但罗斯很清楚,这些同样充满趣味的杂志却是全国性发行,无法准确地传达出纽约的韵味。
举止粗鄙的罗斯最终创造出一份趣味高雅的杂志,是因为他成功地捕捉到新一代纽约人对于幽默感的理解。对于文学艺术的领悟,这份命名为《纽约客》的杂志将笼罩于20世纪20年代的文艺气氛精妙地注入了新闻报道中。
1925年,与新生的《纽约客》在同一幢楼办公的,还有一本仅仅两岁的杂志《时代》。这本杂志创造者之一亨利·鲁斯显然看不起哈罗德·罗斯与他的《纽约客》,认为他追求有趣,却忽略了责任感。但在一点上,这位使命感异常强烈的耶鲁毕业生与乡巴佬罗斯有惊人的吻合,那就是必须把握新世代的阅读需求。
亨利·鲁斯将目光置于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一百万人,坚信这群人应该对世界了解更多,感兴趣的领域更宽阔,而且伴随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个群体还将进一步扩大。他们对于世界局势、科学发现、宗教、艺术诸多领域都会发生兴趣。在《时代》之前,大多数媒体对于新闻的了解仍局限于犯罪、工会与政治,愤怒的声讨大于了解世界的渴望。
两种表征支配了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物质上的极大增长,使城市化趣味最终取代了村镇式美国。就像文学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回忆的,这群出生于19世纪末的年轻人,在二十多岁时发现记录着他们童年往事的乡村已经消失。纽约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使得家乡暗淡无光,享乐主义比起传统的清教气氛更具诱惑。追赶时髦的青年都希望用欧洲味道来掩盖美国的粗俗与贫瘠。罗斯便是这群美国青年中的典型一员。在阿尔贡金饭店里,他与当时纽约最智慧与狡黠的作家与漫画家彼此谐谑。《纽约客》杂志所追逐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乡土与狭隘气息的幽默,甚至是世故。
国际化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变革。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发现自己已不再是欧洲的边缘,反而要开始领导世界了。鲁斯以极鲜明的姿态表明,《时代》正是为了满足国际化美国青年试图认识世界的欲望。由于对新闻进行分类的编写,使得读者在“半个小时内对一周国际、国内要闻有所了解”。
相比于《纽约客》,门肯的《美国水星》等诸多杂志虽然同样标榜文艺与幽默,却更多抓住的是本地乡土式谐谑,虽然可以在20世纪20年代维持成功,但伴随着其读者群的老化,最终还是失败了。
同样,赫斯特与普利策报系因煽情新闻大获成功,而将自己定位于缺乏良好教育的普通民众上。20世纪30年代初的《时代》杂志编辑部内,充斥着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鲁斯相信,只有这些没什么经验、缺乏传统负担的小伙子,才可能寻找出新闻与众不同的新角度。亨利·鲁斯看到了美国的未来中坚力量,而赫斯特却将自己置于一条不断下滑的曲线上。
倘若历史允许横向比较,鲁斯与罗斯为今日的中国媒体人提供了极富参考意义的坐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认为,1890年到1920年是美国的第三次觉醒期。城市化进程使得城市人口迅速扩张,基础建设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使得愤怒与不满在城市内迅速蔓延,而财富的迅速两极分化同样激起社会不公正心态,人们一面奋不顾身地追逐物质,一面又对失去了村镇式恬静生活感到万分迷惘,结果使得煽情新闻与黑幕揭发运动备受欢迎。伴随物质条件的进一步改善,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愤怒,而新群体普遍接受了更良好的大学教育,也使得他们比起周围环境来,更关注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渴望更丰富的生活。
至少从外在表象来看,今日中国同样正在由城市化与国际化两种趋势驱动着。尽管遭受颇多质疑,中国的新一代城市青年正在崛起。他们缺乏传统的束缚,喜欢新兴事物,就像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青年言必谈巴黎,今日的中国青年同样对于国际化充满兴趣。将中国的新一代群体定义为消费主义的一代,或视之为只知物质享受与文化符号,这种理解是肤浅甚至粗暴的。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青年不仅学会了巴黎的时髦打扮与调情方式,也同样亲近了欧洲的文化传统。喜欢亨利·福特制造的T型车与迷恋广播电台,同样表明他们正在建立一种新文化形态,汽车与无线电波同样暗示了年轻的心灵对于自由与宽广世界的追逐。
城市化与国际化这两个名词的背后,蕴含着对狭隘地域观念的背叛,是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运用理智而非情绪、协商而非争执来解决问题。至少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来说,变化已经发生。
但显然,正如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媒体,今日的中国媒体人仍旧生活在惯性思维中。的确,他们曾经依靠煽情、“扒粪”、武断和庸俗的市民化获得过成功,但是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看待未来。这不仅意味着媒体人需要了解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更需要他们本身拥有全新的心态,能够理解城市化与国际化到底意味着怎样一种视角。知道互联网、即时通信软件与邦·乔维(Bon Jovi)并不意味着你清楚地了解新一代群体,而是要知道在一切表象背后,隐藏自由竞争、人人平等、心态开放与个人主义这样的真正含义。
我不断提及新一代中国青年,并非意味人人都去投身青年市场。没人说《时代》《纽约客》是青年杂志,但他们却把握了新时代的特征,成功地繁荣了八十年,尽管他们曾经新颖的角度也最终可能陈旧。
今日的中国媒体,同样需要这种新视野,并伴随未来中国共同成长。一个愚蠢的媒体人会死守今日的市场,一个成功的媒体人则会目光远大地盯着正在上升的曲线。知道当亨利·鲁斯在1929年创办《财富》杂志时是如何设想的吗?他觉得当时的美国商人大多懒散与狭隘,缺乏社会责任感,美国需要心胸开放的新型资本家。鲁斯看到了商业必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核心,所以希望《财富》能够帮助塑造一个新兴资本家群体。从本质上来讲,当时的《财富》肯定缺乏读者,因为那个群体是鲁斯凭空想象出的。但结果却是……
- 微信号
- 网站问题、用户注册登录请联系站长,看到第一时间及时回复。
-

- 公众号
- 慧眼看每日荐书,关键字找书,新功能陆续增加中,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