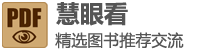编辑推荐
1.近代中医在“废医案”的洗礼下,团结起来自觉寻求中医的出路。在西医细菌学的冲击下,中医学人不放弃对传统气论的坚守,仍然以《伤寒论》等经典医书为圭臬,以中医的“毒”、“疠气”等概念对应“细菌”,对细菌说并非全然排拒,而是主动融会贯通。在形势紧急之下,他们追求中医在学理上的被认可,对中医医籍和医案有所整理与吸收,对中医技术则少有发展。在他们的奋力自救下,中医得以幸存,而对中医技术的发展则是他们留给后世的待完成的使命。
2.近代知识分子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全面审视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有全盘吸收和保守主义两种态度。同样,他们对中医的态度也出现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其中医者以余云岫和恽铁樵为代表,其他知识分子以鲁迅和章太炎为代表。也有人既尊崇民族医疗传统,又吸收西医实验技术,如于右任以西医实验诊断病名,又以传统中药来治疗疾病,收到好的治疗效果。在民族自信深受打击的近代,知识分子对本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矛盾心理可见一斑。
3.现代中医如何走出百年来“废医案”的阴影,在中西医并存的医疗体制下有更大的作为,是近代中医留给现代中医的历史使命。近代中国国运衰微,传统文化包括中医式微,幸而文脉未断。而今民族自信高扬,如何继承中医的优秀传统并发展之,如何摆正中西医的位置,也是现代中医面临的时代课题。
内容简介
近代中医面临“废医”的生死存亡考验,一旦失败将万劫不复。基于传统气论与细菌学的近代中西医博弈,既是一场学理和技术的博弈,更是一场话语权和生存权的争夺。博弈的结果是西医胜出,中医在自救中得以幸存,为重生赢得一线生机。
近代中国国运衰微,中国传统文化也面临危机,中医同样如此。而今,抗生素的弊端日益明显,中医的技术价值也在发扬,如青蒿素的发现,这一切都说明这场关乎中西文化冲突的博弈至今没有停止。
本书立足于以中国医学视角书写中国现代史,聚焦近代中医学与细菌学的各种交锋、对话、排拒与汇通,力图重现中医在西医的科学实验及一步步占据国家卫生主权的过程中,如何运用自身的外感热病知识体系构建中医式的传染病学,并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中医理念和药物可以发挥效用的空间。重现这段历史,意在唤醒中医对自身体系的认识与自信、变革与创新,帮助大众了解中医文化的价值,走出百年来“废医案”的阴影,也为个人的实际治疗与日常养生,提供另一种思考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皮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医疗史与人文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医医史文献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医疗社会史、疾病史、身体史、中国近代战争与科技方面的研究。著有《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台湾日日新——当中药碰上西药》、《“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外感热病的知识转型与日常生活》、《国族、国医与病人——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合编《卫生史新视野——华人社会的身体、疾病与历史论述》、《药品、疾病与社会》。
前言
序 中医抗菌事,得失寸心知
张仲景的《伤寒论》无疑是中国医学史上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这部向被视为众方之祖的医书,也多被看作是中国临床医学的开山之作。该著在宋以后,开始受到诸多医家的推崇而日渐正典化,到明清时期,伴随着张仲景医圣地位的确立,《伤寒论》也渐趋成为与儒学中的《四书》相类的医学经典。与此同时,明清特别是清代的医家,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温病学说”。这一学说,在诸多的中国医学史论著中多被看作是明清医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以是观之,我们应该可以毫无疑义地认为,对“伤寒”、“温病”等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乃是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些疾病,按照今天的疾病分类,大体均可归之于外感性疾病,即由致病病原体导致的感染性疾病,也就是广义的传染病。按照当今医学的认识,这类病原体种类甚多,其中主要有细菌和病毒,不过在20世纪病毒被确认之前,学界和社会往往都以细菌名之。这也就是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于由病菌引发的外感性疾病的诊治,不仅是中国医学关注的重点,也可谓是其特长。
然而吊诡的是,尽管近代以降,张仲景和《伤寒论》的地位不断地被确认和提升,一代代的中医学人也对“伤寒论”和“温病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做出了极其丰富的研究和建构。然而,放眼现实,却不得不承认,治疗由病菌引发的外感性疾病,早已不是中医的主战场,甚至在一般人的认识中,中医已然退出,这一阵地成了西医的专长和天下。就此而论,中原大学的皮国立博士从细菌或者说抗菌入手,来探究近代中医的发展和中西医论争,正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和要害。
国立兄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医疗史的研究,他成长于医疗史研究氛围十分浓郁的台湾史学界,并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是两岸中国医疗史乃至近代史领域中拥有广泛影响的中青年学者。近十多年来,国立兄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在我印象中,他应该是中国医疗史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最具学术活跃度的学者之一。他继以唐宗海为中心来探究近代中西医汇通之后,抓住这一关键议题来展开对中西医论争背景中近代中医演变的研究,不仅充分说明了他的勤奋和积极进取,更展现了他敏锐的学术眼光。
无论是中西医论争还是近代中医发展,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议题,要想就老议题说出新意趣来,抓住问题的要害、提出好问题是关键。国立兄希望从对细菌学说的应对入手,来展现和思考近代中医的“再正典化”过程,无论是选题还是立意都十分巧妙而有意义。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我的考量,大概不外乎以下两点:
首先,应得益于他对近代中医学人诸多论述的深入钻研。国立兄早年围绕着唐宗海,对近代特别是晚清中西医汇通学说有颇为深入的研究,后来大量研读了民国时期恽铁樵等诸多中医学人论著,正是这样系统细致的阅读,使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中医学人对西方医学的关注点从生理学转向了细菌学,从而促使他将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其次,也源于他对中医的现代性拥有颇为清醒的认识。在很多人的认识中,中国医学是从中国这片土地起源和发展起来的治疗疾病的知识体系,从古到今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就已成形,并在当今的中医教育体系中仍为“活着的经典”,而且阴阳五行、虚实寒热、针刺艾灸甚至“辨证论治”等旧有的概念和方法也似乎古今一脉。故尽管中医知识古往今来时有发展,但根本上,其乃是一种本质性的存在,其本质早在先秦、秦汉时代就已经确定,后代的变化不过在其根本体系上做些修修补补而已。中医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瑰宝,而且还是中国唯一活着的“古代科学”。这样的看法,在当今中国医学史和中医学论著中甚为流行,甚至几为定论。既然中医是传统,是古今一脉的本质性存在,自然无所谓现代中医或中医的现代性了。
不过事实可能未必如此,我们不妨从现代有关中医的基本认识入手来做一剖析。现代说到中医,大家几乎都会毫不犹豫将“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视为中医的根本特征和优势,然而现有的研究已经雄辩地表明,“辨证论治”理论和方法与“整体观念”,虽然在近代以前的医学中不是全无踪影,但不仅很少有人论及,更无人将其视为中医学的根本特色和理论。1949年以后,受“西学中”和“大力发展中医药”等政策的影响和驱动,一批医界精英在“科学化”和“国学化”双重理念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民国时期诸多论述的基础上,成功地构建了“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两大理论,不仅填补了因为抛却阴阳五行等而导致的中医核心理论的空缺,而且还构建了一个与西医不同的中医形象,并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进而言之,以西医为参照对象而被视为传统的当下中医,若从中国医学自身的演进脉络来说,实为“现代”。当代中医乃是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渐被质疑甚至否定,以及西方医学的强势进入和日益迅猛的发展,一代代中医学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努力用现代的科学和学科思维,通过医学史钩沉和传统医学知识筛选,逐渐建构起来的一套现代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中医并不是一种作为传统象征的本质性存在,也不是脱离中国历史文化而孤立存在并自足发展的,而是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而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
不用说,国立兄很清楚这些。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才会提出近代中医“再正典化”的问题。围绕着“菌”、“气”、“伤寒”、“温病”等概念,通过对民国时期诸多以中医学人为主的文人论述的细致梳理,国立兄向我们展示了近代中医是如何消化西方细菌学说,并将部分理论和知识化入旧有概念之中的。在科学化、专业化的大潮中,诸多中医先贤们或出于生计的考虑,或因为自身的文化情感,或缘于民族的情怀,面对日渐强势的西方文明以及西方医学,奋力自救,最终使中医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有了可以立足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对于民国乃至当代中医学人在科学化和专业化潮流中对中医的重新塑造,尽管今天不时会受到部分主张回到传统的中医人的批评,但必须说,这些成果无疑是时代文明和一代代中医知识精英智慧的结晶。而且在我看来,他们的努力总体上也是相当成功的,毫无疑问,中医在当代中国能够成为体制内与西医并存的医疗体系,他们的努力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还存在着种种的问题,并不尽如人意,但中医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专业和医疗体系,至少在形式和机制上,其学术的表达形式、知识的传承和教育方式以及医疗机构的运作模式等,都可谓已成功地融入现代社会。
尽管如此,若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却又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中医在努力自救、不断追求自我发展的过程,也正是在与西医竞争中不断失势、主战阵地日渐退缩的过程,何以如此?个中的原因自然是纷繁复杂的,不过有个基本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西医在治疗感染性疾病上之所以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显然不是西医的理论有多么高深,道理有多么动人,而是因为在细菌学理论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明了抗生素这一对付病菌的“魔弹”。反观近代以来诸多中医知识精英的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将最大量的精力似乎用在如何使中医具有科学性和合法性,使其理论逻辑自洽、华丽动人,从而能得到政界和民众的支持而得以自存上,而比较少致力于提升具体的医疗技术。这一事实提醒我们,近代中医发展虽然成绩巨大,但方向是否有值得重新检讨之处呢?
国立兄虽然在书中并没有直接提及这些问题,但他在《自序》中言:“除了历史知识外,期待读者也能省思现代中医的发展与定位,不是为了与西医争胜,而在于治病济世、造福全人类。”实与吾心有戚戚焉!我和国立兄都是历史学出身,历史学无疑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但通过拜读他的文字,我时时能体会到他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对中医的关注。这在往往被称为外史的医疗社会史学界的同仁中,可能是少数吧。正因如此,体会到这份我们共同的志趣,每每让我感到欣慰和鼓舞。应该也与这一情怀有关,近些年,我总在积极倡言医史研究要打破内外史的壁垒,实现内外史的融通。国立兄说法虽与我有所不同,主张探究“重层医史”,即希望通过“重层医史”的探讨,来实现医学学术和日常医疗社会探讨勾连和贯通,其旨趣大概也是一致的吧。
理想的阅读很大程度上乃是读者和作者心灵的沟通,正因为有这些心意相通之处,阅读该著,对我来说是种愉快的体验,不时产生的学术启益自令人欣喜,而常常感受到的意趣相投,更让人深感慰藉。故此,我实在没有理由不郑重向读者推荐这部兼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好书。不过与此同时,我还想说,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远航,特别是对年轻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来说,更是如此。虽然我们可能已在已有基础上尽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远没有到可以停下来自我欣赏的程度。如果按中医学界一些学者或许有些严苛的要求来自省,我们的研究对于中医发展究竟带来怎样真正的启益?“重层医史”,究竟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医疗实践的角度展现对医学知识的型塑?对如此等等的问题,显然,史学界年轻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恐怕一时还很难有底气给予满意的答案。这样的话,那我们又如何可以让别人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中国医学的核心地带了呢?
毫无疑问,我们念兹在兹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未来的路还很长,是以聊赘数语,一者向国立兄新著的出版致贺,二者也略陈学习心得,就教于国立兄及学界同仁,以期共同推动这一研究的蓬勃发展。
余新忠
2019年1月26日于津门寓所
自序 有“生命”的医疗史
中医和西医的会面、碰撞与汇通,是近代医学史无法回避的主题,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个人做学问之路,无甚可称述,在此仅表达一份幸运与一份感激,落笔数言,以示对读者之负责。
笔者自从攻读硕士班开始,即踏入“生命与医疗史”的研究领域,得以一窥中国医学之堂奥,分析它在近代碰到的挑战,并探索一代学人寻求出路之可能。晚清之时,中西医的碰撞主要在解剖与生理学上的争端;至民国之后,中西医则转而在细菌学和病理学上争胜。以后者牵涉到实际治疗和中国医学以“内科”伤寒学、温病学为主的核心理论体系,所以不论在疗效或学理上的争端,其牵涉之广、言论之激,皆超越前代。本书主轴,即为书写民国以来的疾病与医疗史,在整体细菌学上的争议。个人对中医学理本极有兴趣,虽无能行医济世,但总还能从历史学的角度,提出一些对中医发展的观察。在中西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近代中医同西医在热病治疗学的较量上,完全没有屈居下风,值得读者省思。若是连“喊战”、“抗战”都没有资格,日子久了、特色暗淡了,那么中医的“生命”也将走向尽头。史事可鉴,研究中医者能不警醒乎?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起自晚清,最初多在解剖生理学内交手,学理上之争论实大于疗效上的争胜,应该说,中医疗法在当时仍有一定的优势。不过,进入20世纪初,西医在细菌论上取得重大突破,接连成立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在防疫等卫生政策上全面向西医靠拢,而于教育政策上又处处限制中医发展。当时中西医博弈的焦点就在“废医案”的提出,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根据该部组织法,旗下设立中央卫生委员会,以作为卫生决策的议决机关。当时担任委员者,无一具有中医背景。第一届委员会于1929年2月23日在南京召开,会议上以“中医妨碍全国医事卫生”为由,提出四项针对废除中医的提案,分别是《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统一医士登录办法》、《限定中医登记年限》和《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等,统称“废医案”。最后通过并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内容简单归纳即:不允许中医办学校,并取缔中医药相关之“非科学”新闻杂志,进而逐步取消中医执照登记,采取渐进手段来限制中医,最终达到完全消灭中医的目标。随后,上海等地的报纸首先揭露中央卫生委员会的会议内容,舆论一阵哗然。至3月17日,遂有上海中医协会组织,在上海举办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组织晋京请愿团,决定至南京中央政府各机关请愿,终于将“废医案”阻挡下来,赢得中医发展的一线生机。这是全国中医界的首次大团结,用各种力量和渠道去争取自身权益的重大运动,值得现代中医省思。
笔者以为,该运动实为“现代中医史的开端”。在此事件与运动发生之前,中西医之间的博弈或融通,不过是基于学术上的兴趣和文字讨论,采用与否端看中医个人的抉择;但此运动发生之后,中医界自晚清以来所尝试的组织学会、出版医报与串联团结、诉诸媒体舆论、冀求政治与法律上平等的诸般举措,一夕之间都变得“必要”。而学习西医要怎么学,如何科学化,中药疗效和实验步骤为何,中医知识体系如何转型以因应变局等问题,全部都成了中医在博弈中取得生存空间与持续发展的迫切要事。可以说此事件促使中医界迅速在各方面进行变革,以至于我们今日所认知的现代中医逐渐和传统中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与断裂。怎么处理传统中医理论、典籍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成了近百年中医史的主旋律。以史为鉴,我们正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从历史中我们得知中医现状与处境之由来。细菌理论既然是西医在20世纪初取得的最大成果,中医在这场博弈中当然要努力证实自身于对抗细菌、治疗传染病上的优势与技术。而这段历史恰恰揭示了,中国医学唯有不断变革创新、顺势转型,强化治病的技术,才能永不退潮流,在日益激烈的中西博弈中取得一席之地,此为近代中国医疗历史的重大启示。
在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思考上,近代史家,笔者最推崇吕思勉。吕氏低调而踏实,在学术上绽放之光芒虽不及傅斯年、顾颉刚等民国学人来得耀眼,但实际著述成果则远超多数民国学人。他更撰写《医籍知津》,成就了名著《中国医学源流论》的基础。吕氏曾言:“予于教学,夙反对今人所谓纯学术及为学术而学术等论调。何者?人能作实事者多,擅长理论者少,同一理论,从事实体验出者多,且较确实,从书本上得来者少,且易错误。历来理论之发明,皆先从事实上体验到,然后借书本以补经验之不足,增益佐证而完成之耳。”历史研究必与实际相结合,才能谈读史之用。吕氏更谓,历史若脱离实际生活,则为“戏论”,史家不可能对当代之事茫然无知,夜夜闭户读书,而最后有所得者,这是他对历史功用的实际认识。此数语即笔者经历的小幸运。作为中国医疗史研究主体之“中医”,不但仍持续存在,而且生机盎然,为多数历史陈迹、故纸学问中所难能可贵者,为探讨近代中国文化出路的最佳史学课题之一。此端也即笔者有求于读者的:除了历史知识外,期待读者也能省思现代中医的发展与定位,不是为与西医争胜,而在于治病济世、造福全人类。如此才可谓本书具有“生命”,乃中国医疗历史与文化所赋予的“生命”,在西方的挑战下,曲折碰撞、汇通新生,而依旧昂首阔步、独立自主之谓也。
最后,要表达一份感激。本书旧版,得诸位学界先进厚爱,依序由吕芳上、黄怡超、张恒鸿、张哲嘉、刘士永、苏奕彰等先生撰写序言。其他欲感谢之学界师长、中医同道、朋友,皆已见于旧版自序《一位史学工作者生活与研究的自剖》,此书不再重复。简体版新问世,蒙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撰写新的推荐序,使本书增色不少。2006年,笔者第一次到大陆发表医史论文,就是受到余老师的邀请,此书于大陆问世,这份机缘此刻也显得特别有意义。书内除增添新的研究外,也新增了章节,并全面“瘦身”,尽量省去较为冗长的脚注,以便阅读更顺畅。终归文字简练有功,总算有些新意。最后感谢中华书局上海公司原总经理余佐赞先生、责任编辑吴艳红女士,在这段时间给予出版工作上的一切支持。他们对编辑工作之热情与选书之慧眼独具,是本书得以问世的重要催生者。
皮国立
2018年12月于中原大学
- 微信号
- 网站问题、用户注册登录请联系站长,看到第一时间及时回复。
-

- 公众号
- 慧眼看每日荐书,关键字找书,新功能陆续增加中,敬请关注!
-